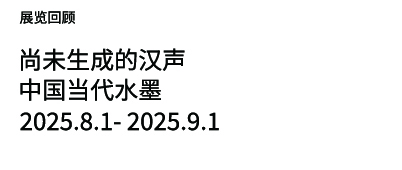
艺术家:栗宪庭、蒲国昌、阎秉会、刘庆和、阿海;学术主持:阿克曼(Michael Kahn-Ackermann)、杨键;策展人:何勇淼;;学术嘉宾:杨键;学术支持:中国美术学院当代水墨研究所
人可艺术荣幸地宣布,将于2025年8月1日至9月1日呈现“尚未生成的汉声——中国当代水墨”。此次展览是人可艺术中心第三次以群展的形式呼唤汉声,由人可艺术创始人何勇淼担任策展人,德国汉学家阿克曼(Michael Kahn-Ackermann)与艺术家、诗人杨键联袂学术主持,中国美术学院当代水墨研究所提供学术支持。本次展览集结了五位中国当代艺术家的逾50件代表性作品,参展的艺术家包括栗宪庭、蒲国昌、阎秉会、刘庆和、阿海。

期待那个人
杨键
我这几代人都没有格,没有格如何在时间里保存?如何在时间里存在?为什么我们失去了格?为什么格从第一义沦落为尘埃,沦落为耻辱,沦落为无价值,而利成为第一义?这是我们对自己文明的背叛,我们还有其他吗?似乎没有了,因此我们把目光再一次投向了古老的过往,他们是如何在变化不定的时间里存在,他们的艺术是如何活到今天而无生死?时间已经过去了千年百年,他们依然可以以心印心,毫无时空的障碍。他们没有纸张没有笔墨只有心,他们有纸有笔有墨但心与纸与笔与墨浑然不分,因此可以以心印心,千年前的不朽人物画下的不朽作品是送给知音的,这是他们的格,我们只有利,转折应该从这里开始,画下的每一笔只有利,没有格,又如何超越生,超越死?时间快要来不及了,我们这几代还能不能出现超越利,超越时间,超越生死的作品?
有时候觉得很悲哀,看着家门口的树,甚至院子里的树都完成了超越,我们这几代连家门口的树都不如,许多人都死了,它们还活着,一天比一天超拔。
其实画一直没变,是画下面的那个人变了,其实那个人也没变,只是那个人的心变了,其实那颗心没变,只有积习在加深,最后成为我们的主人。我们的相一直在变,最难回到的就是君子相与文人相,我们的巅峰状态本来是由君子和文人创造,不是趋于利的小人创作的,那个核心之流,山可以传其魂,水可以传其魄。为什么我们失去了魂魄,只剩下最实际的,并且只关注此生,我们因此而失去了魂,几代人不关注魂,此时最落寞最边缘最无助的就是魂,无神无魂,只有貌似人的人,因此,从王维到弘一法师是同一颗心,但是从王维到我们不再是同一颗心,我们已经偏离了那颗心,那颗与天地合一的君子心已经被我们偏离了,心在几代人的艺术里很难出现,画上只是出现了手,就是没有心。
你的画究竟是物理的还是心灵的,是现实的还是非现实的,是此时的还是永时的,根本在于你是向内还是向外,如果你一直向外破坏会一直持续,直到某一天你向内了那个破坏才会稍稍停息,前所未有的向外也是前所未有的破坏,因此我们一直没有安宁没有休息没有凝定,因为我们一直在向外,从未向内,向内,向内这是最迫切的,因为在心的层面,我们毫无进步,已经自己认不出自己,我们搁浅在这里,没多少人幸免,这是一个基本事实。几代人都看着外面,很少看向里面,主人不再是我们自己,而是我们看着的外面,向外和向内,纯属两种人生,两种艺术,两种文明。
某大学浓荫蔽日,每一栋楼都有古藤缠绕,古树遮阳,新来的主管喜欢阳光,因此古藤古树都被废除,浓荫蔽日从此成为最美的记忆,这是转换的失败。某某人长年吃素,看到了鱼却总是想去抓,这是转换之难。水墨的技术可能也有了,但内在的精神可能并不是我们自己的,无真无诚,只是自我遮蔽,自我干扰,生命被利替代,而非格,放弃了格,我们就放弃了进入历史,在那个生命之流里就像交了白卷一样,这是转换的根性之难。范宽的雪景寒林图多么像一颗巨大的摩尼宝珠,那是日积月累地朝内朝内朝内带来的转换,带来的脱胎换骨,也许我们只有朝内才有转换的希望,那可能正是高贵的灵魂之所为。
一张画只有手,没有心,一张画只有情绪,没有心,一张画只有即将到来的利,没有心,一张画只有父亲,没有慈悲的母亲。
艺术为传神而来,传物之神,传人之神,有些艺术家早年即可通神然后传神,有些艺术家要辛苦一生直到晚年方可通神然后传神,神并不神秘,只是日积月累,真的见到了,但他从不是一个获得者,只是个服务的,为那个循环往复的,为那个一派天真的,为那个元气淋漓的而服务。人之神不能因物而沉沦不现,普天之下都为你的神你的格惊讶,你能将它显现,普照天下吗?谁是其中的那一个?
究竟是谁画下了第一笔和最后一笔?画不足道也,格第一,没有格,转换如何完成?这是真正的转身处,这里不能转身,那就并无希望可言。一个时代走到了真和诚都寥寥无几,这是悲哀和悲剧。艺术由最高之人,最高之格完成,这是汉声之根底。
2025年7月19日
艺术家

学术主持
阿克曼
学术主持
杨键
策展人